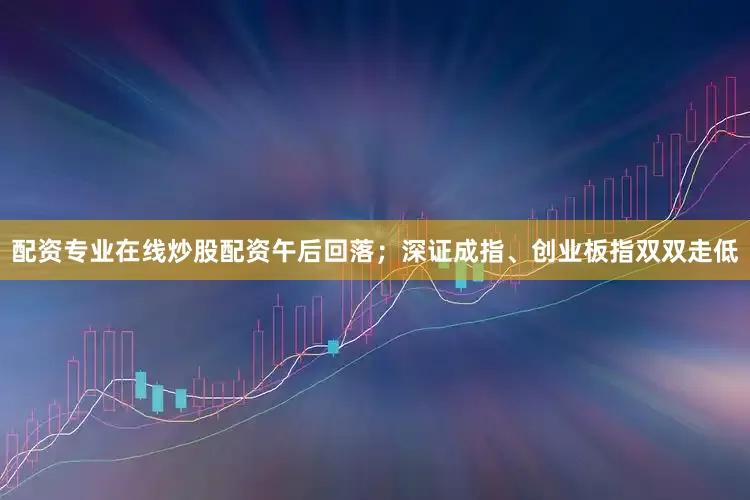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?同样一盒由同一家公司、在同一个车间生产的救命药,为什么在美国卖出的价格,能比在欧洲、日本甚至邻国加拿大贵上好几倍,甚至十几倍?
难道美国人买到的是“镶了钻”的特别版吗?
当然不是。
就拿大名鼎鼎的“药王”修美乐(Humira)来说吧,一种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生物制剂。在美国,它一年的治疗费用,曾经可以轻松突破8万美元。
而在瑞士,这个价格大概是2万美元。

这是怎么回事?难道美国的空气里有什么神秘的“价格催化剂”吗?
很多人会告诉你,这是“自由市场”的代价。美国鼓励创新,高昂的药价是为了补偿制药公司那动辄数十亿、耗时十多年的研发成本。
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道理?就像你花大价钱买了一部最新款的旗舰手机,你是在为它的尖端科技和研发投入买单。
但如果我告诉你,这个“自由市场”的解释,可能只是故事的一半,甚至是精心包装过的“童话”呢?
真相,往往隐藏在一个更复杂、更像“俄罗斯套娃”一样的体系里。要理解这个体系,我们得先忘掉“买家”和“卖家”这种简单的交易模型。
在美国的医药世界里,牌桌上至少坐着三位重量级玩家:制药巨头、保险公司,还有一个你可能没听说过的神秘角色——药品福利管理者(PBM)。

让我们一步步揭开这层迷雾。
首先,登场的是制药巨头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药厂”。
他们是价格的制定者。一款新药上市,他们会定一个非常高的价格,这个价格叫做“批发采购成本”(Wholesale Acquisition Cost),我们通俗点,可以叫它“官方标价”或“建议零售价”。
这个价格有多离谱呢?就像你去一家奢侈品店,看到一个包标价10万。这个价格高得令人咋舌,但它却是整个游戏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。
药厂会说:“我们投入了巨额的研发资金,承担了巨大的失败风险,这个价格是合理的!”
这话有一定道理。研发新药确实是一场豪赌,90%的药物都会在临床试验中失败。但问题是,药厂的开销里,花在市场营销上的钱,往往比花在研发上的还要多。
这就像一部好莱坞大片,制作成本可能1.5亿美元,但全球宣发的费用,可能也要1.5亿甚至更高。你买的电影票,一半是为电影本身,另一半是为那些无孔不入的广告。

所以,那个高昂的“官方标价”,既包含了研发成本,也塞满了营销费用和……嗯,你懂的,巨额的利润。
好了,第一位玩家出牌了:一张标价10万的“天价牌”。
这时候,普通人肯定买不起。于是,第二位玩家登场了——保险公司。
按理说,保险公司应该是我们普通人的“盟友”,对吧?我们每个月交保费,他们就应该站出来,撸起袖子跟药厂砍价,把药价打下来。
“你这药太贵了!不降价,我的客户们就不用你的药了!”
这听起来很美好,也是我们想象中应该发生的事情。
但在现实中,保险公司很少亲自下场“肉搏”。

为什么?因为他们也怕麻烦,而且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于是,他们请来了一位“金牌砍价师”。
这位“砍价师”,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神秘角色,整个美国药价迷局的核心——药品福利管理者,简称PBM(Pharmacy Benefit Manager)。
PBM是谁?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“超级团购团长”。
保险公司对PBM说:“我这有好几千万的会员,你去帮我跟各大药厂谈,让他们把药便宜点卖给我们。谈得好,我给你服务费。”
于是,PBM就手握着几千万甚至上亿人的“采购大权”,浩浩荡荡地去找药厂了。
现在,好戏才真正开始。
PBM走到A药厂面前,A药厂的药“官方标价”是1000美元一盒。

PBM说:“老兄,你这药太贵了。这样吧,你给我一个60%的折扣,也就是600美元的‘返点’(Rebate),我就把你这款药,列入我的‘优选药品目录’(Formulary)。这样一来,我覆盖的几千万病人,都会优先使用你的药。”
A药厂一听,虽然要吐出600美元,但能换来巨大的市场份额,划算!于是,成交。
接着,PBM又走到B药厂面前。B药厂也有一款类似的药,可能效果差不多,但“官方标价”只有500美元。
B药厂说:“我的药本来就便宜,你看,我给你一个20%的折扣,也就是100美元的‘返点’,怎么样?”
现在,请你站在PBM的角度想一想,你会把谁的药放在“优选目录”里?
是那款最终价格为400美元(1000-600)的A药?还是那款最终价格为400美元(500-100)的B药?
从保险公司和病人的角度看,两款药最终价格一样,似乎没差别。

但对PBM来说,差别可就大了!
因为PBM的商业模式,在很多情况下,它的收入是和“返点”金额挂钩的!它能从药厂给出的“返点”里抽成。
也就是说,A药厂给了600美元的返点,PBM能分到的蛋糕就更大;B药厂只给了100美元的返点,PBM能分到的蛋糕就小得多。
你猜,PBM会怎么选?
它会毫不犹豫地选择A药厂。它会回去告诉保险公司:“A药厂的药更好,我已经帮你们谈下来了!”
发现这个游戏里的“魔鬼”了吗?
这个体系,根本不鼓励药厂生产“低价药”。恰恰相反,它鼓励药厂把“官方标价”定得越高越好!

因为标价越高,可以操作的“返点”空间就越大。一个标价10000美元的药,给个70%的返点(7000美元),远比一个标价3000美元的药,给个10%的返点(300美元),更能获得PBM的青睐。
这就像一个商场里的促销游戏。
药厂是专柜,PBM是商场请来的“促销活动策划人”,保险公司是商场本身,而我们病人,就是来逛商场的顾客。
A专柜的商品标价1000元,B专柜的同类商品标价200元。
“促销策划人”PBM对A专柜说:“你参加我的‘满1000返600’活动,我就把你的海报贴满商场所有电梯口!”
PBM又对B专柜说:“你的价格太低了,没什么返利空间,不好做活动,吸引不了人。”
结果,整个商场都在宣传A专柜的“巨额优惠”,顾客们蜂拥而至,感觉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。他们不知道,隔壁B专柜的商品,不打折也比A专柜打完折还便宜。

更要命的是,商场(保险公司)和促销策划人(PBM)的收入,都和A专柜的“高标价、高返点”模式深度绑定。标价越高,流转的资金越多,他们能分到的利润也就越多。
这就是美国药价的第一个核心秘密:一个由药厂、PBM和保险公司共同构建的“高标价、高返点”的利益闭环。
在这个闭环里,价格信号完全失灵了。竞争不再是围绕“谁的最终价格更低”,而是围绕“谁能给中间商提供更高的返点”。
那么,谁是这个游戏里唯一的输家?
当然是最终的买单者——病人。
你可能会说,不对啊,我有保险,保险公司和PBM不是已经把价格从1000美元砍到400美元了吗?我应该也受益了啊。
问题就出在这里。你的保险条款里,写的可能是“你需要支付20%的共同保险(Co-insurance)”。

关键是,这20%是按什么价格来计算的?
在很多情况下,它是按照那个虚高的“官方标价”1000美元来计算的!
也就是说,保险公司和PBM享受了折扣后的400美元净价,而你,却要支付1000美元的20%,也就是200美元!
你实际支付的药费,占到了药品真实成本(400美元)的整整一半!
而那个没有保险的人呢?他可能要硬生生面对那个1000美元的“官方标价”。
这个游戏玩到最后,药厂维持了高利润,PBM赚得盆满钵满,保险公司也通过复杂的保费和自付设计锁定了收益。只有病人,在为一个被层层放大的“价格泡沫”买单。
还没完,这个体系还有一个“终极守护者”——美国独特的法律环境。

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发达国家,政府都是一个强有力的“超级买家”。政府的医疗保健系统会直接代表全体国民,与药厂进行价格谈判。
这就像一个国家的“医保局”说:“全国人民的药都从我这里买,你要么给我一个全球最低价,要么就别想进入我的市场。”药厂根本没有多少议价能力。
但在美国,情况恰恰相反。
长期以来,美国法律竟然明确禁止政府(特别是为老年人提供保险的Medicare计划)去和药厂进行价格谈判。
你敢信吗?全世界最大的单一药品采购方,被自己国家的法律捆住了手脚,被禁止“砍价”。
这相当于把一只饿狼和一只被绑起来的羊关在同一个笼子里,然后说,你们“自由”博弈吧。
结果可想而知。

直到最近几年,《通胀削减法案》才刚刚赋予了政府极其有限的、针对少数几种药品进行谈判的权力。但这对于整个庞大的体系来说,只是撕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。
所以,我们现在可以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了。
为什么美国的药价全球最贵?
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“为创新买单”的自由市场故事。
它更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“赌场”。
药厂是庄家,他们设定了赔率(官方标价)。保险公司和PBM是赌场的“叠码仔”,他们不关心谁输谁赢,只关心赌桌上的流水有多大,因为他们的佣金是按流水比例抽成的。为了让流水更大,他们甚至会和庄家联手,鼓励赌客们玩那些赔率最高、最刺激的游戏。
而病人,就是走进赌场的赌客。无论你觉得自己运气多好,赢了多少“返点”,只要你坐上这个赌桌,从长期来看,你永远是输家。因为整个赌场的规则,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你设计的。

这个体系,层层嵌套,环环相扣。高昂的研发成本是它的“借口”,复杂的PBM返点是它的“核心玩法”,保险公司的精算模型是它的“安全垫”,而法律对政府议价权的限制,则是它屹立不倒的“保护伞”。
最终,美国人支付的天价药费,不仅是在为新药研发买单,更是在为这个庞大、不透明、且极度昂贵的“中间商体系”买单。
他们买到的不是“镶了钻”的药,而是被裹上了一层又一层“金融泡沫”的药。
所以,下次再有人告诉你,美国药价高是纯粹的自由市场和创新精神的体现时,你或许可以给他讲讲这个关于“超级团购团长”和“赌场叠码仔”的故事。
曼雅配资-股票网上开户-股票配资网官网信息-股市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